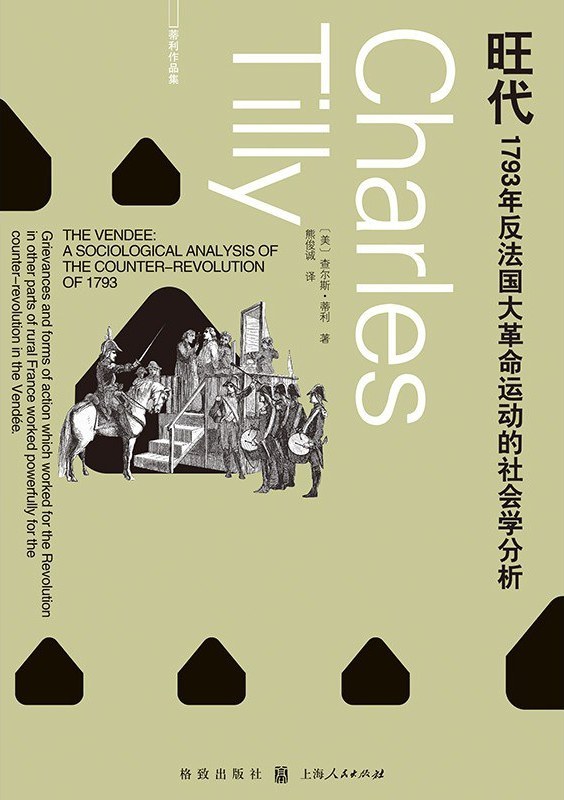
《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美]查尔斯·蒂利著,熊俊诚译,格致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420页,98.00元
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著有五十一本书,其中十八本已被翻译成中文。蒂利涉猎广泛,包括城市社会学、国家形成、民主、社会运动、劳工和不平等一系列主题。但是,他的第一本书却是历史题材,讨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外省”的反革命运动。
旺代(Vendée)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农业省份,与中国的“黄泛区”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法国的屡次革命和反革命运动里,被外界赋予了各种意义和任务,沦为“被牺牲的局部”。《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The Vendé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1793)跳出了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争——共和制和君主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旺代地区叛乱运动的形成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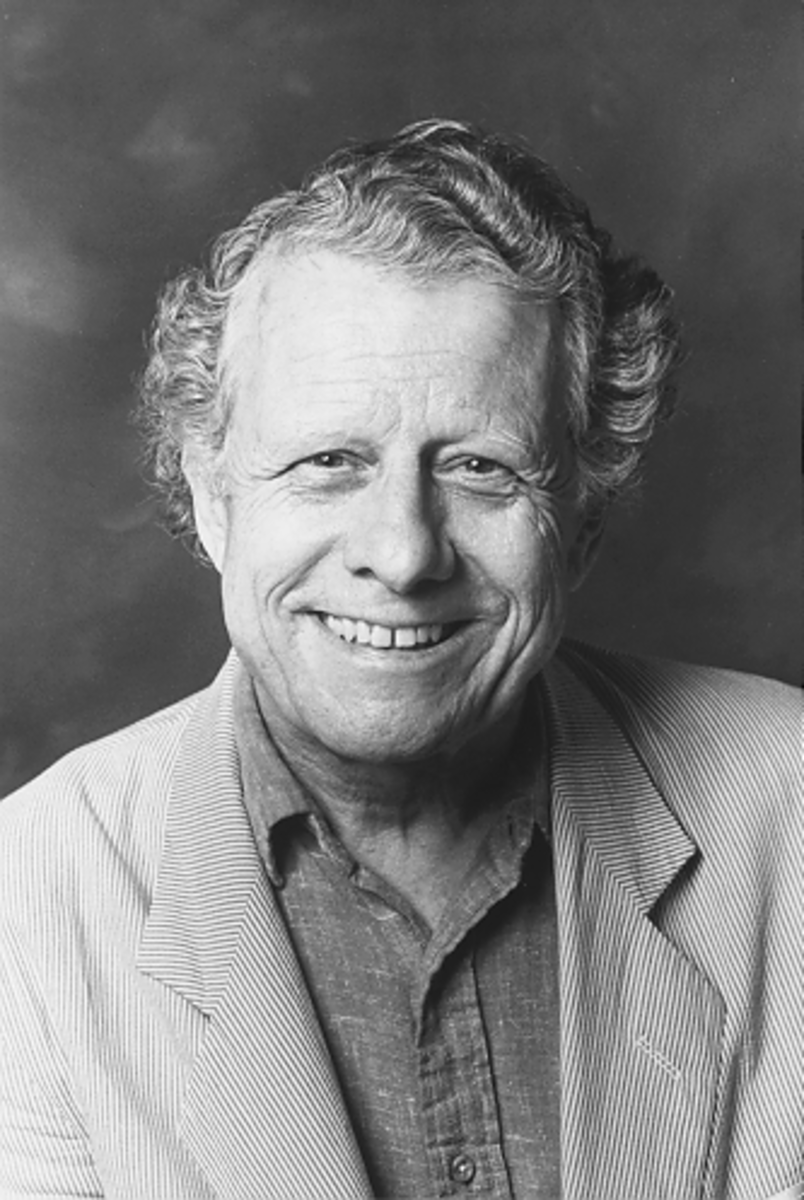
查尔斯·蒂利
一
旺代因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旺代战争而闻名于世。这场战争中,农民起义者(白军)与革命军(蓝军)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冲突,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1892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为了打败外国干涉军,法国共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加税,招募三十万军队。恰逢1791年《教士公民宪法》颁布,教会的许多权力被剥夺,法国前国王路易十六支持外国干涉军帮助自己复位,在1793年被处决。于是,许多势力以宗教和国王为旗帜掀起了针对共和政府的叛乱。1793年初,法国共和政府在八十三个省里最多只控制了三十个省。蒂利写道:“政客们选择‘旺代’这个词,是希望给这场运动强加一种相当简化的形式……某些历史学家感到疑惑,为什么是旺代省而不是法国其他地区。这个问题提得很糟糕。事实上,在旺代起义时,许多地区陷入混乱:西部和西南部的卡昂和波尔多成立了独立政府,东南部的土伦向英国人投降。”
尽管法国其他地区的叛乱被镇压,但在旺代周边的暴动经久不息,形成了一大片叛乱地区,大约有十个省,历史学家称之为“军事旺代”。叛军于1793年4月组建了一支“天主教皇家军队”,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波及大半法国西部。秋季,共和军重新占据了优势,并于10月攻占了叛军控制的最重要城镇绍莱。战败后,旺代军队主力渡过卢瓦尔河,向诺曼底挺进,孤注一掷地试图夺取港口,并获得英国军队和法国流亡者的援助,但在大西洋岸边的格朗维尔(Granville)被击退,最终于12月被彻底歼灭。
从1793年冬到1794年春,共和军在“旺代军区”实施了暴力镇压。在城市约有一万五千人被枪杀、溺毙或送上断头台,而在乡村,约有二至五万平民被地狱纵队(colonnes infernales)杀死,许多城镇和村庄被烧毁。1794年12月,共和军与旺代各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并在1795年2月至5月期间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一次旺代战争”。1795年6月,“第二次旺代战争”爆发。然而,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领导人要么屈服,要么在1796年被处决。此后旺代地区还经历了短暂的叛乱,包括1799年的“第三次战争”,1815年的“第四次战争”和1832年的“第五次战争”,规模都小得多。据估计,五次战争遇难人数约为二十万,其中包括约十七万名旺代军事居民,占起义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关于旺代战争的历史研究,对于中国学界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国外对它争论已久。旺代战争史的研究领域,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阵营:被称为“蓝军”的革命派,被称为“白军”的旺代派。
在波旁王朝复辟后,“白军”第一批出版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文本。最著名的是《德·拉罗什雅克兰夫人回忆录》(Mémoires de Madame de La Rochejaquelein)。德·拉罗什雅克兰夫人的教父是复辟国王路易十八,她丈夫的哥哥——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Henri de la Rochejaquelein)是旺代叛乱中最年轻的将军。她在书中将旺代战争描述为一场自发的农民起义,其目的是保卫国王和教会。
波旁复辟王朝倒台后,“蓝军”的代表、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路易斯·沙桑(Charles-Louis Chassin)出版了十一卷档案和回忆录,批评旺代叛乱。他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秉持共和主义观点,否认这场运动具有群众性质,认为它是贵族和牧师筹划的阴谋,民众出于无知才盲目跟风。
此后,两大阵营的研究特点基本形成。“白军”主要站在保皇党和天主教立场,认为这支农民军必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贵族有着深厚的感情,目的是重建王权并拯救天主教。他们主要依赖旧贵族和神父收集和传播的口述证词,关注1793至1794年共和军镇压的暴力行为,喜欢使用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调。而“蓝军”以专业学者为主,倾向于档案和其他实证材料。为了区别于对手,“蓝军”刻意避免苦难叙事或唤起共和派的情感——即便许多共和阵营的“爱国者”在旺代战争期间被杀。
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社会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引入,历史研究发生了变化。在“白军”和“蓝军”之外,出现了第三类作者。如法国的保罗·博伊斯(Paul Bois)、马塞尔·福舍(Marcel Faucheux)和查尔斯·蒂利。他们认为,这场起义的导火索并非1791年教士的民事宪法和1793年路易十六的处决,而是旺代地区长期的贫困。革命未能实现1789年三级会议里的承诺:旺代省的大多数人口是佃农,他们未能从废除封建权利中获益。虽然王国和贵族的财产被拍卖,但主要惠及资产阶级和商人。从那时起,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大规模征兵使青壮年人口聚集,成为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蒂利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和人力,首都巴黎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作为外省的旺代则被单方面无度索取。即使国家从封建时代进入共和时代,旺代农民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善。随着反法同盟战争的爆发,政府派发的税收和徭役激增,引发了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旺代叛乱只是一个最为激烈的例子。然而,由于这类作者没有迎合“白军”的叙事,也被后者归为“蓝军”。
二
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里引用了蒂利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后期之前,欧洲各地的陆路交通十分昂贵,没有有效的水路交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担大规模军队和城市所需要的谷物和其他物资供应。为供养内陆城市,统治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并支付高昂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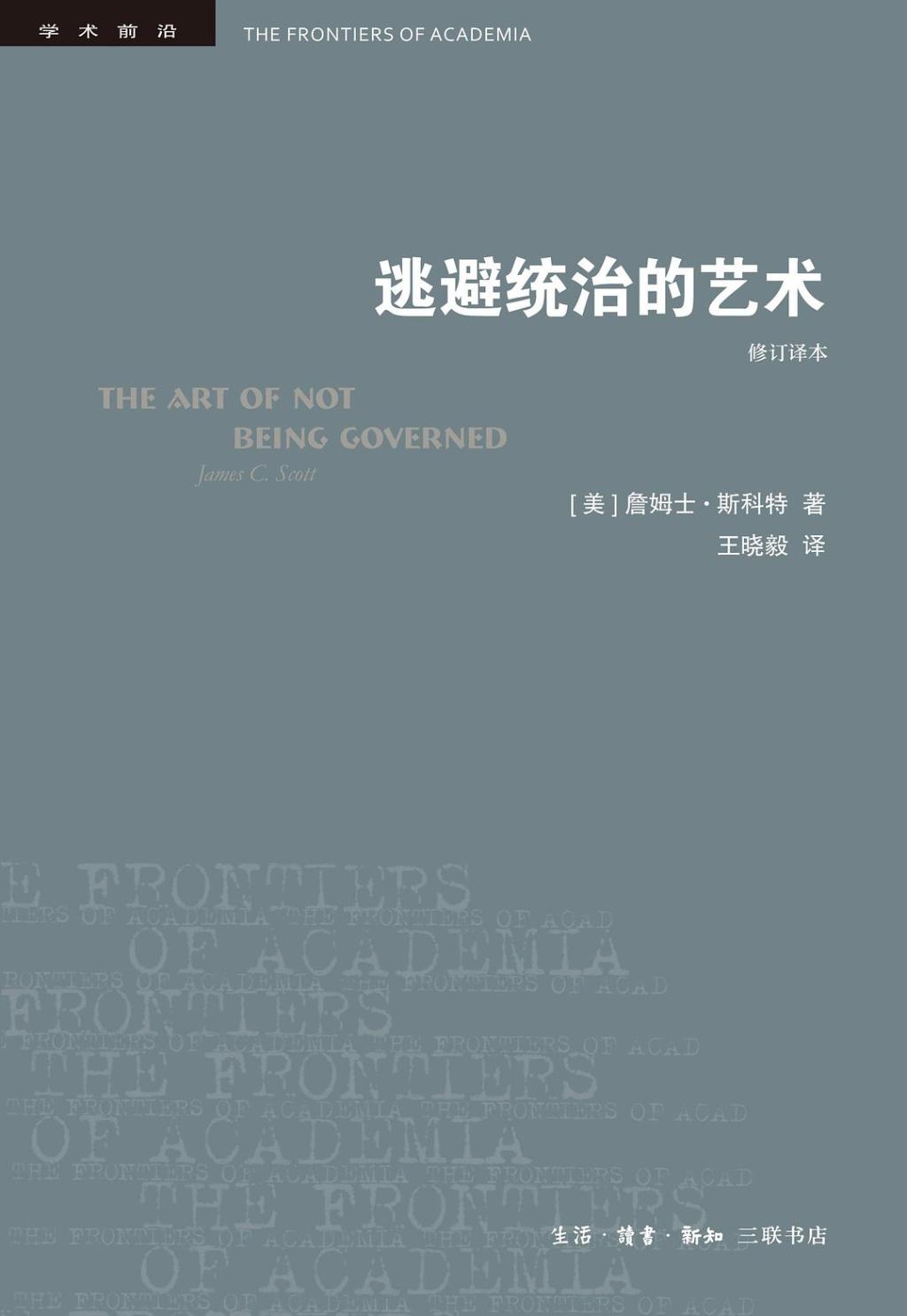
詹姆斯·斯科特著《逃避统治的艺术》
十八世纪,法国的税收普遍增加,总税收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此外还有各种特别税,种类繁多。法国大革命后,旧制度虽然被废除,但民众的负担并没有减轻。新的行政等级制度出现,城市资产阶级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持续的欠收造成农民境况恶化;共和政府滥发货币并强行摊派赋税,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政府的不公正和专断措施加剧了人们的失望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叛乱,而征兵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793年2月,国民公会投票批准征兵三十万人,征兵方式是从各市镇的未婚男子中抽签选出。3月3日,在瓦卢尔省的绍莱(Cholet),有五六百名年轻人拒绝被征兵,与当局发生了流血冲突。随后,叛乱波及法国西北部的十几个省。
蒂利认为,对故土的眷恋、对服兵役的敌意以及对“异域”的恐惧——这些被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反复提及的主题——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切。政府突然征调了三十万士兵,他们不知被派往何处,要么加入追击顽固神父的军队,要么去保卫一个令人憎恶的政权。至于公务员和市政官员,却免于服役,因而被民众视为压迫者。体格健全的男子离开后,其余民众更容易受到国家滥权的侵害,因此被迫叛乱。值得注意的是,1789年《人权宣言》具有国民议会成员未曾想到的重要意义,即反抗压迫。该文件明确指出:“任何限制人权的政权都是滥权的,必须予以反抗。”因此,他认为“旺代起义”既合法又正当。
拉瓦雷纳市(La Varenne)市长雅克·雷杜罗(Jacques Redureau)回忆叛乱的情形:“大约五十名武装人员,有的手持长矛和镰刀,大多数手持步枪,前往拜访公社的居民。他们强迫所有找到的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否则将被处死。然后他们去了公社之家。”在法国大革命后设立的公社之家,叛乱者打破了文件柜,拿走了所有法律、法令和其他文件。第二天,叛乱者让妇女们把文件带到中心广场烧毁。在梅斯尼尔昂瓦莱、圣弗洛朗和尚托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样,“证书和文件”被焚烧。叛军还攻击了他们所憎恨的政府的象征:国民警卫队及其旗帜;税务员、账簿和钱箱。他们把市政府当做一种像巴士底狱一样的堡垒,不同的机构安插着那些作为“革命支持者”的共和派,他们为共和政府提供情报,因此也是未来的镇压工具。大量的市政官员被叛军监禁或处以枪决,市议会成员和共和政府的支持者纷纷逃命。仅在马什库尔(Machecoul)一地,在3月27日至4月22日就有一百五十至两百名共和派被逮捕并枪毙。
1793年3月15日,两千四百名共和军在路易·德·马尔塞(Louis de Marcé)将军的指挥下前往旺代镇压叛乱,19日与叛军相遇。当共和军离叛军很远时,后者故意演奏了《马赛曲》的旋律。士兵们误以为是一支从南特赶来接应他们的队伍,忘记了防备,随后在沙罗桥之战(Bataille de Pont-Charrault)中被击溃。共和军逃回拉罗谢尔,马尔塞被指控犯“叛国罪”,六个月后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这场战役对巴黎的共和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由于溃败发生在旺代省的中心,此后所有西部的叛乱分子都被称为“旺代人”。
作家雨果写道:“在家乡,旺代人是走私者、劳工、士兵、牧羊人、偷猎者、神枪手、牧羊人、敲钟人、农民、间谍、刺客和森林里的生物。旺代是名副其实的迷宫,灌木丛和崎岖的小路交织在一起,只有当地居民知道它的秘密。”旺代叛军擅长游击战和伏击战术,屡次偷袭共和军,后者恼羞成怒,也采取了报复措施。
旺代叛军装备简陋,使用“老式猎枪、十字架、草叉和棍棒、长矛和镰刀”,其武器弹药的补给需要从共和军手中夺取——而且他们并非常备军,农民在战斗结束后会回家干农活。为了寻找具有军事才能的领导者,起义者寻求当地贵族的支持,后者通常是前波旁王朝的军官。例如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他曾是路易十六的侍卫,1792年离开巴黎,退居乡下庄园。据说,一位农民在1793年来找他,宣称邻近教区的居民们渴望加入起义,已经拿起武器,并且请求他担任他们的领袖。被任命为旺代天主教和皇家军队的总司令时,德·拉罗什雅克兰才刚满二十一岁。勒芒(Le Mans)战役失败后,他高呼:“我真希望战死沙场!”此后,他的行动愈加鲁莽,1794年1月在游击战中被打死。

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像,绘于约1816年。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圣鞠斯特(Saint-Just)素有“美男子”之称。为了与圣鞠斯特的形象一较高下,“白军”史学家也将德·拉罗什雅克兰塑造成了英年早逝的俊美男子。描绘德·拉罗什雅克兰战斗场景的油画往往成为“旺代战争”的标志之一。他是在巴黎长大的时髦的公子哥,而旺代乡下人的身影并不起眼,往往在背景里出现。
三
旺代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属于阿基坦公国(Duché d'Aquitaine),后来被法国吞并,在英法百年战争和法国宗教战争里历经战火。在十六世纪,旺代地区拥有大量有影响力的胡格诺派新教徒,一度在纳瓦拉国王亨利四世的母亲珍妮·达尔布雷(Jeanne d'Albret)的控制下。1572年,达尔布雷在谈判期间死于巴黎,原因不明,有人认为是被“毒蛇王后”凯瑟琳毒死的。随后,著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爆发了,许多新教徒死于非命。旺代地区也受到了法国宗教战争的严重影响,这场战争在1562年爆发,持续到了1598年。亨利四世建立波旁王朝后改信天主教,但对新教徒颁布了《南特敕令》。1685年,波旁王朝又废除了《南特敕令》,对新教徒实行严厉的镇压,迫使许多新教徒改宗或流亡。由于传教士路易·德·蒙福特(Louis de Montfort)的影响,旺代地区逐渐成为严格的天主教地区。许多人认为,这为旺代人抵制法国大革命做好了思想准备。
1789年11月,为解决财政危机,法国议会投票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将其转变为国有财产。政府收回教会财产以后,于1790年以教会资产作为支撑,发行“指券”。这一决定剥夺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履行其传统职责——帮助贫困人口——的财政来源。几个世纪以来,教会财产得益于教区成员的遗赠而积累起来。革命前,这些资产由神职人员管理,服务于农村社区。为了偿还“指券”,资产被出售,落入个人手中(资产阶级、农民、贵族,甚至神职人员),他们将其用于个人用途。因此,教区民众普遍感到被掠夺了,并认为政客应对此负责。1790年7月12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在年底生效,规定所有神父与公务员一样,要宣誓遵守宪法;1792年,法国法律规定,所有未宣誓效忠的、引发骚乱或经同一省份六人要求驱逐的神职人员,均应被驱逐出境,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将被处以十年监禁。1793年旺代叛乱爆发后,3月18日的法令更进一步,规定任何被驱逐出境并被捕的神父均应处以死刑。
第一次旺代战争前后,共和政府的官员频繁遭受人身威胁,例子有很多:勒洛鲁-博特罗市长布坦(Boutin)于1794年3月6日被枪杀。1795年,拉沙佩勒-巴瑟梅尔市长第一助理奥班·拉赫姆·杜·帕蒂(Aubin L’Homme du Paty)失踪,三周后被发现溺亡。1795年12月25日,瑟孔迪尼的长官布里约(Brillaud)也死于非命。除了谋杀之外,还有日常骚扰、砸门、砸窗、人身攻击等等。在圣佩雷港(Port-Saint-Père),市政人员宣称,他们每次访问村庄都会被侮辱、殴打。
在共和政府的描述里,神父往往是“躲起来策划暴行”的形象。一则公告写道:“公民们,你们知道是谁在侵犯你们的庇护所,是谁在用犯罪之手攻击你们的人身和财产吗?他们是流亡者,是躲藏起来策划新暴行的神父,是他们的附庸。”但是,很多案子没有证据能证明由神父策划或知情,政治犯罪和普通的犯罪往往无法区分。
被派到旺代镇压叛军的路易·图罗(Louis Marie Turreau)将军在《为旺代战争的历史服务的回忆录》(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Vendée)指出,这些神父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声望,不是由于波旁王朝的高压政策,而是有三个原因:他们生活方式的正直、他们教义训练的严肃性以及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深入了解。大多数神职人员本可以流亡国外,等待更好的时机。他们强迫自己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因为他们确信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农民支持神父,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教会可以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国王可以成为他们的口号。他们接触的信息太匮乏,思维“非蓝即白”,想象不出,也接触不到其他类型的反对派。根据国民议会专员的调查,农村居民往往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只希望拥有值得信赖的神父。专员写道,“为了获得这份恩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愿意缴纳双倍的税款”。
从《旺代》开始,查尔斯·蒂利的研究风格基本形成:在历史分析中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不妄下评判,而是基于事件的过程和形成机制进行分析。1968年,蒂利向艾森豪威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集体暴力的报告。该委员会是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成立的机构,旨在评估民权运动期间的城市骚乱。同年,他发表论文:《欧洲视角下的集体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四
在法国,巴黎和“外省”是两个世界。这种现象在旺代尤为典型。旺代是一个纯农业省,尽管它出产的谷物可以养活三个省的人口,但它缺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既不像卢瓦尔河谷那样拥有前朝王族的文化遗产,也不像布列塔尼和诺曼底那样,有军事贵族割据一方。因此,旺代只能像战利品一样被争夺。基于过去的研究,蒂利在1975年编辑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一书,创造出了“掠夺性国家”理论。在1985年的《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战争制造和国家制造》(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一文中,蒂利将主权者描述为不诚实的,因为“政府本身通常会模拟、刺激甚至捏造外部战争的威胁”,政府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向公民兜售安全的幌子,强迫人民服从,以换取免受政府侵害的保护。他认为战争是“最大的有组织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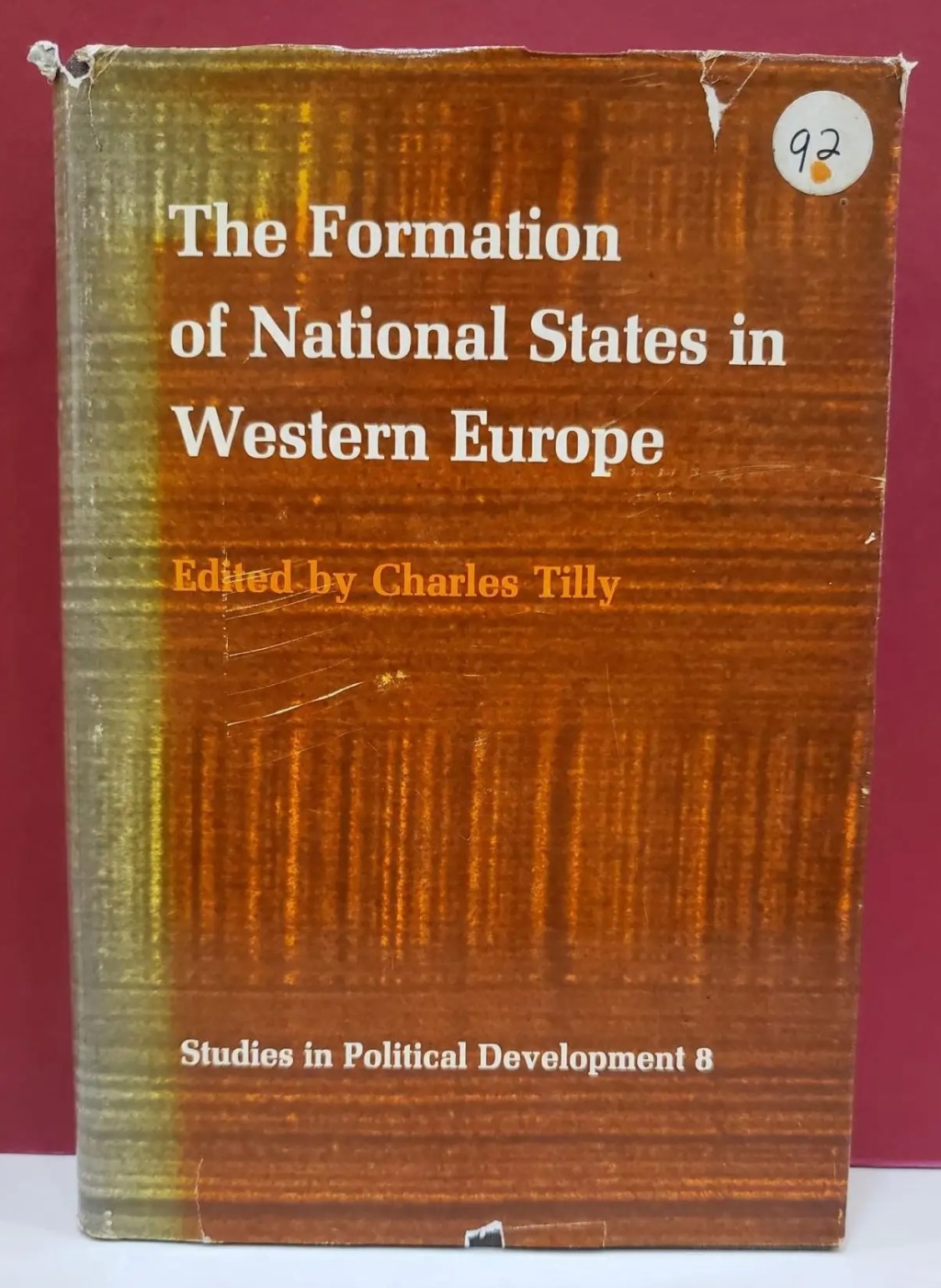
蒂利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旺代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只能由别人来代表,而且往往属于弱势的一方,较为落后的一方。在英法百年战争前,它属于阿基坦公国,在宗教战争期间,它属于胡格诺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它又属于保皇党和天主教会。巴黎的势力如走马灯般轮换,却都不约而同地对旺代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李珂评《旺代》|法国大革命“被牺牲的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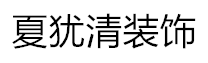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16
京ICP备2025104030号-16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