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法]乔治·米努瓦著,于艳茹译/陶逸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出版,233页,88.00元
有关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文化市场与书籍管制政策,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其独具故事性的笔法,先后为读者呈现了《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等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的佳作。然而,这几部作品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审查制度的反对者,而较少系统探讨审查方的立场与动机。在另一部尚无中译的著作 Censors at Work 中,达恩顿虽然涉及波旁王朝时期的文字审查制度,但更多是将其作为与英属印度和民主德国的制度比较案例,并未深入梳理法国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与运行模式(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至于其他相关研究,往往从印刷术技术史的角度切入,对审查的社会政治机制关注不足(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NLB, 1976;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Volume I and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学者乔治·米努瓦(Georges Minois)的《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补充。米努瓦生于1946年,是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历史学家。他兴趣广泛,善于在长时段中追索思想的变化脉络,同时文笔流畅,多有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米努瓦在此书中由印刷术诞生写起,直至法国大革命,系统梳理了法国文化审查制度的演变与实践特征。米努瓦尤其强调,由于监管主体的多元性及其相互牵制,审查制度始终存在可供利用的“缝隙”,使得达恩顿笔下的“地下文学”得以蓬勃发展,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审查本身。然而,这并非“自由最终战胜专制”的故事,因为言论审查并未随着旧制度的瓦解而消失——它依旧是任何政治体制的常备机制,自由的真正边界至今仍有待界定。
“Censure”的宗教-道德底色
现代语境中的“审查制度”(Censure)通常被理解为世俗公权力对公共言论的限制,包括文字、图像及影音等。米努瓦以印刷术的诞生作为开头确实是合理的逻辑起点。然而,针对印刷文字的审查仅是对Censure较晚近的理解,若追溯其词源,这个概念源自拉丁文动词censēre,原意为“评估(如财产)”或“主张”(某种意见或判断),延伸至政治领域后,演化为罗马共和国时期监察官(Censor)的监察职责(censura)。共和国时代的监察官负责执行人口普查,这是确定公民身份及其附带的财产与相应公民责任的重要仪式。该仪式的高潮部分即为所谓“净礼”(lustrum),意味着整个罗马公民共同体进行象征性的洁净与神圣重塑。因此,监察官具有一种带有专断色彩的道德审查权(moral censure),能够将违反规范者贬斥为“重赋公民”(aerarii)或处以“声誉污损”(infamia)等社会性惩罚(Andrew 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9-112)。
进入基督教拉丁语语境后,该词又获得了“神罚”(censura divina)的含义,施加于那些冒犯了上帝的罪人。至16世纪以后,censura 才逐渐演化出如今最常见的意义:出于政治或警察目的而对书面材料实施审查与删除("Censure",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informatisé (TLFi), CNRS, en ligne ; Alain Rey (dir.),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Le Robert, 2011. 法国语言学家乔治·杜梅吉尔进一步探讨了该词的印欧词源,意为“通过公正地评估,赞扬或谴责,将人与行为置于等级体系中的正确位置上”。参见 C.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td., 1980, pp. 50-51)。可见,在欧洲历史语境中,“审查”一词的底色是带有严厉宗教-道德色彩的概念,它并非单纯作为世俗政权维持统治秩序的手段,而首先是针对违背规范者的公开谴责与社会排斥,其目的在于维系共同体道德的“纯净”状态。在追溯词源演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米努瓦笔下的审查制度在17-18世纪间转变的深刻意义。
多方博弈中的制度缝隙
正是由于审查最初具有的强烈道德意味,因此教会最早承担起审查的责任。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米努瓦写道,“主流价值被全社会一致地分享、体验和内化”,异见是罕见的,且很容易被镇压(《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第1页)。异端并非不存在,但其思想限于手抄文稿与口耳相传的网络,难以跨越地域形成广泛影响。印刷术的普及改变了这一格局。天主教会在最初对这一技术持欢迎态度,利用其传播经文和教义;然而,当普通信众可以直接阅读《圣经》并产生独立于教士的个人诠释时,异端滋生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索邦大学的神学博士首先采取行动,要求禁绝一切有损正统信仰的著作,以维护教义纯洁。相比之下,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的态度较为务实,其宽松并非出于思想自由理念,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司法程序与管辖权,这也使其与索邦在审查事务上多有摩擦。
王权一方面依赖索邦和高等法院来监控思想舆论,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授予出版特许(privilège)来直接掌控印刷业,这引发了高等法院的强烈反对。米努瓦强调,王权的禁书政策往往缺乏原则性,更多受制于短期政治利益,这种反复无常进一步加剧了多头审查机构之间的矛盾。理论上,审查的流程是“索邦检举、高等法院审判、王权决断”,但现实中各方频繁越权与绕权,这些裂缝也为反审查作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尽管存在内部争夺,三方在抵制罗马教廷干预法国事务的“高卢主义”立场上相对一致,这种政治文化使普通天主教教士在面对罗马与巴黎时不得不做出忠诚选择。然而,教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文盲农民,他们虽对神学争论兴趣不大,却容易被宗教情绪动员,因此天主教在新教的压力下,开始编撰“教义问答”并推动农民识字,以稳固信众。宗教战争期间,激进的天主教同盟(La Ligue catholique)利用王权衰落之机,严厉清洗了受王权庇护的、倾向异端或人文主义的出版商,并将宗教多样性视为“专制暴政”的征兆,因为这意味着任意裁量的人治取代了无可置疑的“神意”。于是,这一时期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倒置——教会和民众反而在逼迫王权采取更强硬的审查立场。这深刻体现了世俗政权和宗教权威对于审查目的的巨大分歧。
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与绝对君主制的逐步确立,王权在17世纪开始成为审查制度的主导力量。这并不意味着索邦大学或高等法院丧失了审查权,而是审查的目的与逻辑发生了转变:在教士主导下,审查旨在根除异端思想;在王权主导下,则以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为最高目标,重在维护王权尊严、世俗秩序与国家统一。黎塞留与马扎然不仅与宗教力量结成同盟,继续打击被视为“有害”的思想,还通过建立法兰西学院和《法兰西公报》等机构,集中控制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并借助学院体制引导学术创作,为颂扬绝对君主制的学者提供津贴。同时,他们加强对出版特许权的管理,从制度上约束印刷商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一套兼具“禁绝”与“引导”的舆论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的社会控制模式提供了雏形。
然而,世俗权力并不关心信仰意义上的“灵魂纯洁”,只要不直接挑战王权尊严,审查当局往往无意对思想进行彻底改造。这为某些思想流派留下了生存空间:如笛卡尔主义在表面顺从权威的同时,凭借逻辑与理性的自主性削弱了传统论证的基础。冉森主义者的策略则是“形式上的服从、内心的保留”,以消极抵抗消解审查的实效。但更根本的限制来自旧制度内部的权力分散。绝对君主制本质上是中世纪社会结构演化的产物,并不能反过来彻底重塑社会:索邦与高等法院仍尽力维持自身独立性;在国家承担义务教育之前,教会继续牢牢掌控基层社会。贵族与官员虽然是体制的受益者,却常为启蒙思想提供庇护,如沃邦元帅、孔代亲王、蓬巴杜尔夫人等皆曾支持或保护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法国处于欧洲多国体系之中,受到迫害的作家与出版商往往能够逃亡至相对宽松的联合省或瑞士,继续其写作与出版活动。
正如米努瓦讽刺的评论,“审查制度只对那些不畅销的作品才显得有效”(《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93-94页)。那些异见作家的畅销书,一旦被列入“禁书”,反而身价倍增,刺激了走私与盗版的巨大市场。这一现象在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以及迈克尔·卡瓦斯(Michael Kwass)的《走私如何威胁政府》中都有生动的呈现(迈克尔·卡瓦斯,《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另见,Jeremy D. Popk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770-1800”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412-436)。比较遗憾的是,米努瓦在出版特许与审查背后的经济动力方面着墨较少,没有把审查制度置于资本主义版权理念形成的背景下探讨,这使他丧失了和英国出版审查制度的比较机会,削弱了该研究本应有的深度(关于英国出版与版权制度的研究,参见Ronald V. Bettig, Copyright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stview Press, 1996)。
到旧制度末期,审查几近形同虚设,即便路易十六亲自下令谴责《费加罗的婚礼》,也无法阻止该剧在精英圈内的热烈追捧。米努瓦评论说,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已然失控的政权面前,而上层贵族却毫无自觉地陶醉在反叛潮流之中,正兴高采烈地锯断自己所栖的树枝”(《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201页。此处根据法文原版重译)。
米努瓦的研究不仅描绘了旧制度时期审查制度的形成与运作模式,还揭示了其在实践中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法国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得益于“开明君主制下的温和审查”——禁令从未消灭过一种思想,反而往往保证了作品的成功。虽然这种“舆论泡沫”并非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但旧制度的审查史留下了一条重要教训:在一个内部权力分散、外部存在多国体系的社会中,依赖单纯的禁止来阻断思想的传播是徒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制度末期的审查制度确如米努瓦所言,已经“过时”了。
“旧审查”的进化
米努瓦将大革命视为旧制度和审查制度的终结,这一判断或许过于绝对。实际上,与旧制度一同毁灭的不是审查制度本身,而仅是审查的“旧制度”。进入19世纪的法国,审查制度虽不再以宗教正统或君主权威为名,却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履行控制社会的功能。马丁·里昂(Martyn Lyons)的《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工人、女性与农民》揭示了,资产阶级通过推广阅读,将工人、女性与农民等“边缘”群体——在当时亦被称为“危险阶级”——逐步纳入主流社会规范。这意味着夺取政治权力后的资产阶级从葛兰西意义上的“运动战”(直接的政治夺权)转向“阵地战”(长期的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过程漫长而潜移默化:19世纪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尚未完全摆脱旧贵族的影响,同时还需应对新兴无产阶级文化的挑战。然而,借助义务教育、成熟的新闻出版体系和更系统的舆论引导,资产阶级逐步建立起文化主导权——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总结,这种“文化霸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之后才真正巩固。
当代西方社会普遍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言论自由”原则,但广义的审查依旧存在。与旧制度时期不同,今天的文化审查更多通过制度化的平台控制(如法律层面的“合规要求”)和社会规范的塑造(如“政治正确”所引发的自我审查)来实现。那些被视为“不宜传播”的作品,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公开查禁或焚毁,而是淹没在海量的文化产品中,通过算法推荐、市场选择与舆论引导逐渐被边缘化,失去公共讨论中的“可见度”。这种转向意味着,审查已从显性的压制,变为隐性的过滤与淡化,其效果虽不如旧制度时期那般直接,却同样在塑造可被主流社会接受的言论边界。
译文勘误
米努瓦对旧制度时期审查制度的分析,确实为理解西方社会控制模式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然而,中文版中不时可见一些颇费猜测的译句,有的甚至让人忍不住去翻原文,以确认是否真如中文所呈现的那样。
例如,第10页谈到教士大会时,译文写道:
它在1585年创立了一种制度,一种表达和控制手段,直至旧制度末期的教士大会为止。
紧接着下一段末尾,又突然出现一句:
但不必过于强调这个特点,我们来谈谈法国的主教会议。
两句之间既无语义上的衔接,也无逻辑上的递进。翻检原文可知,更贴近原意的译法应是:
虽然罗马几乎已无法再干预法国的文化事务,但法国教会却在宗教战争期间,利用王权一时的衰弱,于1585年设立了一个机构,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延续至旧制度终结的重要发声与控制平台:教士大会……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称作一场法国主教团会议,这样的说法并不算太夸张。
原句的主语是“教士大会”,其中“直至旧制度终结”只是持续时间的限定。但译文将其理解为制度的“终点”,完全改变了句子的重心。更有趣的是,“On peut parler de…”这种带缓和语气的判断陈述,被处理成了引入新话题的“我们来谈谈”,而“sans trop durcir le trait”(并不算夸张)的细微转折则被忽略,使得整句话在中文中显得既突兀又莫名。
第30页的例子,则出现了理解错误。译文写道:
1562年,王权和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总是突然地直接出现……国王却被高等法院和巴黎宪兵队队长禁止“给与任何印刷许可,陛下的宣告没有任何效用”。
原文其实是:
1562年,王权与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终于直接爆发……同时禁止高等法院和巴黎警政长官(prévôt)再行发放任何印刷许可,并声明若此前已发放许可,其“自即日起皆为无效,毫无法律效力可言”。
这里不谈将 directement 译为“突然地直接”这种多余叠加,也不论 prévôt 被译作“宪兵队队长”是否合适,最核心的问题是主宾完全倒置:原文的“Il est défendu au Parlement et au prévôt de Paris…”是典型的法语被动态结构,即“禁止某人做某事”,主语是国王,下达禁令的也是国王。译文却将“被限制者”翻译成了“发出禁令者”,于是王权的行使,摇身一变成了王权被压制。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第139页。原文是审查官莫罗对米拉波的一句鼓励:
您的学问越广泛传播越好;只要简化些术语,没人敢攻击您的学说。
译文则成了:
您的科学不能广泛流传;简而言之,我们不敢攻击您的学说。
一句原本带有善意的鼓励,变成了带有禁止意味的婉拒——这不仅扭转了语义,也改变了原本的历史语境和人物形象。
以上几例明显错译仅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典型,全书中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在词义上“别出心裁”,如第12页将索邦大学与高等法院之间的权力角力(se jouer)译作“戏耍”,第63页把“克洛维受洗”变成了“血洗克洛维”;有的则是对比喻或引申义视而不见,比如第135页的“établir une espèce d'intelligence…”在此语境下显然是“勾结”或“默契”,译文却直译成“智慧类型”;还有的干脆凭空添加,例如第8页的“圣职人员在王权实施中只是一个虔诚的象征”,在原文中难以找到对应。至于将文森·瓦屈尔(Vincent Voiture, 1597–1648)译成“伏尔泰”,或将19-20世纪的政治术语套用在17–18世纪的语境中,这些“跨时空”的用法虽富想象力,却也让读者很难还原原著的历史风貌。
某些历史典故和术语的处理,则更像是“留白”——例如“Stagirite”是亚里士多德的别称(取自其出生地),译文直接音译为“斯塔基特里”,不加说明;对涉及的神学或政治派别,例如法国宗教战争时期的“政略派”(Les "politiques")与“天主教同盟”,也无必要的背景注释(译文将其译作“政治派”或干脆错译为“政治家”使读者感到迷惑。所谓“政略派”泛指在宗教战争时期主张宗教妥协、反对极端派别、以国家统一和君主权威为最高政治目标的温和政治力量。他们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温和新教徒或宗教立场不甚鲜明的贵族与法官。该派在结束内战、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与王权立场一致,但在具体宗教政策上偶有分歧。“Politique”一词在当时语境下往往带有贬义,尤其在“天主教同盟”宣传中,被指为“为政治利益出卖信仰”的人。参见 Emma Claussen, Politics and 'Politique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A Concep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这些细节虽然不如重大错译那样显眼,却在无形中削弱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准确性。
作为一部以旧制度时期审查制度为主题的研究,米努瓦的著作不仅补充了我们对法国启蒙运动与权力运作模式的理解,也提示了一个更广泛的议题——审查并非某种历史偶然,而是任何社会治理都可能采取的技术与策略。在他的叙述中,权力的分散、制度的缝隙以及多国体系的存在,共同塑造了法国旧制度下的文化景观,也为“被禁之书”的传播提供了土壤。遗憾的是,中文版在翻译质量上与原著的水准并不匹配,对于有能力阅读法文的读者,原著无疑是值得推荐的;而对于依赖译本的读者,则需在阅读过程中保持必要的谨慎与辨别。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张翼评《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缝隙中的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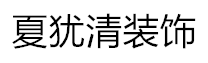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16
京ICP备2025104030号-16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